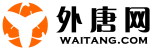许国璋电视英语的相关介绍
- 许国璋,人名,同名人士有语言学家,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同时也在位于江汉明珠的沙洋师范任教。另有同名人士,著名爱国将领,下面分别详细介绍。 许国璋,1915年11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34年6月毕业于苏州东吴中学,同年9月入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他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同时也在位于江汉明珠的沙洋师范(今荆楚理工学院)任教。
1994年9月11日,许国璋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人生评价
许国璋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党。新中国刚刚诞生,他就远涉重洋,许国璋回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在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孜孜不倦,忘我工作,倾毕生心血于我国的外语教育和语言研究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历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卷》副主编等职,曾获国家教委和北京市高教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许国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他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从60年代初开始,通行全国,历30多年而不衰,成为我国英语教学方面同类教材的典范。他积极倡导外语教学改革,他的一系列有关英语教育的论文和演讲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珍惜人才,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为我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世人熟识许国璋,大多是通过其主编的《许国璋英语》。《许国璋英语》自六十年代问世年以来,影响了几代中国英语学习者,风靡中国英语教学界几十年。九十年代初,许国璋先生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前进,这套教材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修改。在承担着繁重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他硬是挤出时间重新修订了《许国璋英语》,并在外研社出版。重新修订的《许国璋英语》更加受到读者喜爱,十多年来共发行了几百万册。
《新编许国璋英语》则是许国璋先生根据时代的发展,前后花了六年时间,几易其稿编写而成。该书1993年在外研社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而另外一本汇聚许国璋先生众多学术成果的《许国璋论语言》的出版,则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许国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语言大师的慧眼和才智,在语言学诸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论著甚丰,其中《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从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及其语言哲学》等独具创见,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名篇。作为一位睿智的哲人,他在外国文学、翻译和文化研究以及鲁迅研究等学术领域也有许多建树,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许国璋先生襟怀坦荡,表里如一。他一生崇尚真理,热爱科学,为此追求不止,奋斗不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他境界开阔,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热情扶植新生的学术力量,为一代学人之师表。
人生小传
许国璋(中3)先生外号“雪莱”
1915年11月25日,大诗人徐志摩出生18年后,在他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又一位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大学者———许国璋出生了。这是一个勤奋的学子,一个带着诗人气质的青年。他少小离家,先后辗转求学于嘉兴、苏州、上海等地,1930年考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附中。到1934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为全级之冠。
按照当时东吴的惯例,三所附中毕业的前3名可入本校大学部的文、理、法三学院,均减免学费,第一名则全免。但许国璋放弃了这种优待,执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主修管理学,后于1936年9月转入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与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查良铮、李博高等人同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三个多月,北大、清华、南开相继南迁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理、工、法等学院设在长沙城内,文学院则搬至南岳山中,租借圣经学院为校舍。在南岳,聚集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教授,如吴宓、叶公超、柳无忌、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钱锺书、钱穆以及英国诗人及文论家燕卜荪(WilliamEmpson)等。1938年初,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昆明,文、法两院暂设在昆明西南的蒙自。4月5日开学,校名遂更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许国璋先生与夫人学生许国璋在名师的指导下含英咀华,学业精进。晚年的许国璋在他的自传体文章《回忆学生时代》中写道:“从此时起到1939年夏,历南岳、蒙自、昆明三地,过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三年级听燕卜荪课,四年级问学于钱锺书先生,执弟子礼至今。”
许国璋英语地道,独具风格。他喜读18世纪英文散文,尤其是艾迪生(Addison)和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文章,前者纯正、典雅;后者庄重、铿锵。许国璋颇得个中三昧,人们听他的演讲纯属一种艺术享受,而由他译的司马迁《项羽本纪》选段竟得到当时教四年级的汉英翻译课、眼界高、要求严的叶公超教授的激赏,认为颇有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风。
1939年7月许国璋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他先后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外文系任教。1947年12月,许国璋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17世纪、18世纪英国文学。钟情于雪莱、又赢得“雪莱”外号的许国璋,在大诗人雪莱的故乡,圆了他充满诗意的梦,在“康桥”追寻老乡徐志摩当年的浪漫踪迹……
许国璋既是一位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而世人熟知许国璋,大多是通过他主编的四册大学《英语》教科书。许国璋的名字与“英语”成了同义语,已经家喻户晓了。
许老主编的《英语》(即风行至今的《许国璋英语》)出版于1963年,历经30余年而不衰,为国内外所罕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桂诗春教授曾和许老开玩笑说,“许国璋英语”已经成为像英国英语、澳洲英语那样的英语变体了,你看街上不是贴满了“许国璋英语班”的广告吗?桂先生认为该教材之所以能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抓往了两个特点,一是结合我国实际,二是适合成年人自学。
一部《许国璋英语》,受惠者不计其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李良佑先生曾经撰文说:“中国自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现了一个出国热潮。或求学,或工作,或移民,不同文化教育层次的均有出国。我在美国,发现不少人从中国带出去的书籍中都有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我偶尔好奇问之,为何不远万里携带此套教材?答曰:看来看去还是许国璋的实用。”
特异的文风
北京的几位外语界名教授在学术上各有造诣,深孚众望,但就个人
许国璋英语的性格及文章风格,又各有异趣。有的是忠厚长者,慈祥随和;有的才华横溢,然出言下笔谨慎;有的外柔内刚,文笔犀利;有的则是刻意求新,谈吐行文均气热磅礴。许国璋应属最后一类,他学养颇深,涉猎甚广,学贯中西。除英语教育、英美语言文学外,他为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做出了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在翻译、文化史及鲁迅研究等领域也多有建树。
许国璋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他那篇发表在《西方语文》第2卷第2期(1958年5月)的文章《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被全文译载于苏联的《语言学问题》杂志,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60年代,许国璋的研究触角从英国文学完全转入现代语言学。他和朱德熙先生一起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新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调到北外外语研究所担任所长以后,许老更深入、更系统钻研西方各家语言学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部分的学术水平很高,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论著《许国璋论语言》写于许老63至75岁的晚年。许老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介绍Austin,纵论Saussure,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书中那语言学家的慧眼、哲学家的深邃、数学家的精确、文学家的笔韵以及伟大人格的力量,令后人难望其项背。
“南王北许”是当年外语教学界中的流行说法,其中蕴藏着人们对智如泉涌的王宗炎、许国璋二老的爱戴与敬仰,足见他们在中国语言学界确然不拔的地位。
人格的力量
文革期间,许老被隔离、审查、靠边站。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老二公”(指许老及王佐良、周珏良二公)均受到很大的冲击。许老的书都被所谓的造反派贴上封条,但他没什么怨言,对一切都是默默地承受着。他说自己是1957年1月加入组织的老共产党员,惟党是听,惟党是从。
1970年他去了干校,来到湖北沙洋。先住竹棚,后迁入砖房,20多人同居一室,生活诸多不便。据北外庄绎传先生回忆:“许老有个习惯,熄灯后打着手电看一会儿书再睡。过了几天,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要再打手电看书。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打着手电看过书。”“有一天刮大风。窗外有个井架好像快被吹倒了,周围的幔布也像要吹掉。我说咱们把小窗户关上吧,许老说好。等我关上之后,他说:“我在家里一年四季都是开着小窗户睡觉的!”为了其他同志,许老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
在8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么一件趣事,有人说完全可以编进《新世说新语》:常年在北外校门口摆摊儿的一位皮匠师傅托英语系一位教员带话给许老说,您许老是无人不知的名教授,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及我两三天的收入,您有何感想呢?许老听到后又托这位教员回话说,咱们两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审美对象不同。你一锤子下去,砸得准,打得牢,便获得一种美感。我读书写文章,得一佳句,也能高兴好几天。真正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你和我追求的都是成功所带来的美学上的享受。
北外校长助理顾曰国教授难忘“哲人”许国璋先生:“我最后一次与许老交谈是在他作古前一个月。我从教室骑车回家,见到许老由人陪着在花园里散步,就赶紧停下车走过去。他见到我,困难地要向我笑出他那习惯的朗声大笑,可是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我很难过,不过还是设法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他最后叮嘱我的几句话我终身铭记:‘小顾,我听说他们将来要培养你当副校长,你不要推脱,也不要忘乎所以,要好自为之。’”
超越物质的束缚
许国璋是一个真学者,更是一个普通人。
这位睿智倔强的老人,额头饱满而微秃,脸庞清癯而微长,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戴一副深度眼镜。夏天,白衬衫,黑领带。冬天,裹一条长围脖,戴一顶挺洋气的小呢帽。他总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不时哈哈大笑。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称其为“高谈雄辩,誉满士林”。
许先生一直蜗居在从50年代起就没有搬过家的老单元二居室里。当你爬上北外那栋年月最久的楼,推开那扇深红色的门,走过那条长长的门厅,幸许能看见许老在书房靠窗的木椅上读书、看报或写文章,还有室中总摆着的那盆高大的刺儿梅……年届耄耋的季羡林先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
每当有客人来访,许夫人(黄怀仁女士)怕谈话影响许老的工作和休息,总在茶几上放一只闹钟,定时提醒他们中止谈话。而许夫人离开书房后,许老便偷偷地把闹钟的止闹按钮按下。许夫人见闹钟好长时间不响,以为出了毛病。此时许老总是哈哈大笑,酷似一个“老顽童”。许老有一个梦:等英法之间的海峡隧道通了,就带上与他心心相印、厮守终身的夫人从北京坐火车,一直坐到剑桥去!(许夫人有一原则:旅行不坐飞机,立场十分坚定!)如今,许先生带着他诗人般的梦走了。应该说,他对生命的那般执著,远远超出了死亡对他的诱惑。1993年5月下旬,许老从欧洲讲学回到北京,因为多年超负荷的工作而病倒,到了第二年的9月11日因心肌梗塞病逝在家中,享年79岁。
老伴走了,黄怀仁女士仍然日夜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风湿性足疾,惦记着他晚饭后的小睡,惦记着他爱喝的莲花白,还惦记着他最后的一次补牙……许老走了,膝下无子女。然而,许老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又何止千万,许国璋的生命因此而飞越无限……
谈学英语
1.学英语就要无法无天,要天不怕地不怕。
2.学外语,要眼尖,耳明,嘴勤,手快。只要多读,多记,多讲,多写,自有水到渠成之日。
3.学习外语,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不要把自己圈在只读洋文的狭小天地里,一定要具备良好的国学基础。
4.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不要总是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语言。
译文欣赏
〖下列译文为许先生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译文,出自王佐良先生《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42-43. 〗
(原文: I deny not, but that it is of greatest concernment in the Church and Commonwealth, to have a vigilant eye how books demean themselves as well as men; and thereafter to confine, imprison, and do sharpest justice on them as malefactors. For books are not absolutely dead things, but do contain a potency of life in them to be as active as that soul was whose progeny they are; nay, they do preserve as in a vial the purest efficacy and extraction of that living intellect that bred them. I know they are as lively, and as vigorously productive, as those fabulous dragon’s teeth, and being sown up and down, may chance to spring up armed men.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unless wariness be used, as good almost kill a man as kill a good book; who kills a man kills a reasonable creature, God’s image; but he who destorys a good book, kills reason itself, kills the image of God, as it were, in the eye.)
许先生译文:教会与国家,于书之为好书坏书,公民之为好人坏人,不能不表极大关注。此点余亦承认。治坏人,或予禁闭,或投牢中,或处于极刑。然则书非可以致死者也。书之生命力,乃作者灵魂所赋予。书,作家智慧之精华,如炼金丹,升华净化,臻于至纯,乃纳玉壶,以为珍藏。谚言,龙之齿,植地生幼龙。书之孳衍,与龙似。植书于野,异日或生持矛武士。人可以错杀,好书亦可以错毁。是不可不慎也。杀一人,杀一有理性之生命,杀一上帝之子孙耳。若毁一好书,实毁理性本身,无异毁上帝之目 。"